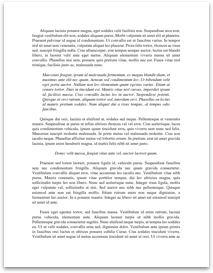从改写理论看郭沫若的翻译
摘要:郭沫若不仅是我国的文学巨匠,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翻译家。他对翻译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主张。本文通过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探讨意识形态和诗学对他翻译活动的操控。
关键词:改写理论 意识形态 诗学 操控
一 郭沫若及其翻译
郭沫若 (1892-1978),原名开贞,号尚武,笔名沫若,是我国著名的诗人,戏剧家,历史家,考古学家,也是中国现代诗歌翻译史上一位杰出的翻译家。郭沫若一生所出版的译著有30种,涉及10个国家100多部作品,总字数超过300万。他的译学理论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作为“风韵译”的发起人,他在英诗翻译研究上树立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和主张,并在翻译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感情和理解。
二 改写理论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①,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等提出了“文化转向”。在这种转向下,“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②这一重大成果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之后勒菲弗尔基于多年对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的研究,在他的《翻译、改写、文学名声的操控》中提出了一套全新,涉及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的翻译理论体系——改写理论。他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 他还认为翻译便是改写,改写即是操控,改写的动机“往往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诗学上的需要。”译者在某种明确的再创造动机下及多种操控作用下参与对原文的改写活动。
三 意识形态和诗学对郭沫若翻译活动的操控
郭沫若的翻译活动始于20世纪初,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这一重要过渡期。随着西方民主浪潮的涌进,中国学者们意识到启蒙和救亡是祖国的迫切需要,除旧,创造,新生成为了社会的主旋律。在“五四”民主及科学精神影响下,歌唱普通劳动者的惠特曼诗歌对郭沫若等作家诗人产生强烈震撼。这种影响显示在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一诗中,郭沫若表达了对劳动者的无限敬仰,反射出了“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的思想。1922年,郭沫若翻译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小说通过少年维特恋爱过程中所遭遇的痛苦,憧憬及绝望,深刻揭露并批评了封建的等级偏见和当时的封建守旧观念,发扬了一种抨击陋习,摒弃恶俗的叛逆精神,进而宣扬了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他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新时代》和歌德的《浮士德》,以及大量雪莱和海涅的诗歌。这些译作让许多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并在中国进步青年之间掀起呼唤革命斗争的热潮。正如郭沫若在《浮士德》附录中谈到:“作品中所讽刺的德国当时的现实,以及曾以巨人式的努力从事反封建,二在强大的封建残余的重压之下,仍不容易拨云雾间晴天的那种悲剧情绪,实实在在和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情绪很像彷佛。”③由此可见郭沫若翻译动机之一是为了鼓舞中国人民为民主和创新而奋斗,这一精神给中国新文学树立了榜样。
其次,勒菲弗尔认为,“为了使外国文学作品易被译入语文化接受,译者需要作些改动以使疑问符合译入语文化的诗学。”这和郭沫若认为翻译过程是一种再次创造不谋而合,郭沫若曾经说过:“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 作为一位诗人,郭沫若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和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到他对诗歌翻译的独到见解: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把握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1923年8月,他在复孙铭传的信中写道:“我对于翻译素来是不赞成逐字逐句的直译。”接着他在《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一文中说:“逐字逐句的直译,终是呆笨的办法,并且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我们从一国文字之中通晓得一个作家的思想,不是专靠认识他的字面便能成功的。”由此可见郭沫若反对生硬、拘泥于字面意思的“直译”。除了研究翻译策略,郭沫若非常重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个人感情和经验的介入,特别是在他翻译雪莱诗歌时,他曾说过:“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莱,我能听得到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罗新璋,1984:334)郭沫若将自己的精神和艺术风格融入了翻译文本,这也是为什么读者在读郭沫若翻译的诗歌时常常感觉不到文化所带来的语言差异。
四 结语...
摘要:郭沫若不仅是我国的文学巨匠,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翻译家。他对翻译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主张。本文通过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探讨意识形态和诗学对他翻译活动的操控。
关键词:改写理论 意识形态 诗学 操控
一 郭沫若及其翻译
郭沫若 (1892-1978),原名开贞,号尚武,笔名沫若,是我国著名的诗人,戏剧家,历史家,考古学家,也是中国现代诗歌翻译史上一位杰出的翻译家。郭沫若一生所出版的译著有30种,涉及10个国家100多部作品,总字数超过300万。他的译学理论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作为“风韵译”的发起人,他在英诗翻译研究上树立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和主张,并在翻译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感情和理解。
二 改写理论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①,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等提出了“文化转向”。在这种转向下,“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②这一重大成果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之后勒菲弗尔基于多年对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的研究,在他的《翻译、改写、文学名声的操控》中提出了一套全新,涉及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的翻译理论体系——改写理论。他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 他还认为翻译便是改写,改写即是操控,改写的动机“往往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诗学上的需要。”译者在某种明确的再创造动机下及多种操控作用下参与对原文的改写活动。
三 意识形态和诗学对郭沫若翻译活动的操控
郭沫若的翻译活动始于20世纪初,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这一重要过渡期。随着西方民主浪潮的涌进,中国学者们意识到启蒙和救亡是祖国的迫切需要,除旧,创造,新生成为了社会的主旋律。在“五四”民主及科学精神影响下,歌唱普通劳动者的惠特曼诗歌对郭沫若等作家诗人产生强烈震撼。这种影响显示在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一诗中,郭沫若表达了对劳动者的无限敬仰,反射出了“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的思想。1922年,郭沫若翻译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小说通过少年维特恋爱过程中所遭遇的痛苦,憧憬及绝望,深刻揭露并批评了封建的等级偏见和当时的封建守旧观念,发扬了一种抨击陋习,摒弃恶俗的叛逆精神,进而宣扬了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他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新时代》和歌德的《浮士德》,以及大量雪莱和海涅的诗歌。这些译作让许多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并在中国进步青年之间掀起呼唤革命斗争的热潮。正如郭沫若在《浮士德》附录中谈到:“作品中所讽刺的德国当时的现实,以及曾以巨人式的努力从事反封建,二在强大的封建残余的重压之下,仍不容易拨云雾间晴天的那种悲剧情绪,实实在在和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情绪很像彷佛。”③由此可见郭沫若翻译动机之一是为了鼓舞中国人民为民主和创新而奋斗,这一精神给中国新文学树立了榜样。
其次,勒菲弗尔认为,“为了使外国文学作品易被译入语文化接受,译者需要作些改动以使疑问符合译入语文化的诗学。”这和郭沫若认为翻译过程是一种再次创造不谋而合,郭沫若曾经说过:“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 作为一位诗人,郭沫若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和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到他对诗歌翻译的独到见解: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把握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1923年8月,他在复孙铭传的信中写道:“我对于翻译素来是不赞成逐字逐句的直译。”接着他在《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一文中说:“逐字逐句的直译,终是呆笨的办法,并且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我们从一国文字之中通晓得一个作家的思想,不是专靠认识他的字面便能成功的。”由此可见郭沫若反对生硬、拘泥于字面意思的“直译”。除了研究翻译策略,郭沫若非常重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个人感情和经验的介入,特别是在他翻译雪莱诗歌时,他曾说过:“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莱,我能听得到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罗新璋,1984:334)郭沫若将自己的精神和艺术风格融入了翻译文本,这也是为什么读者在读郭沫若翻译的诗歌时常常感觉不到文化所带来的语言差异。
四 结语...